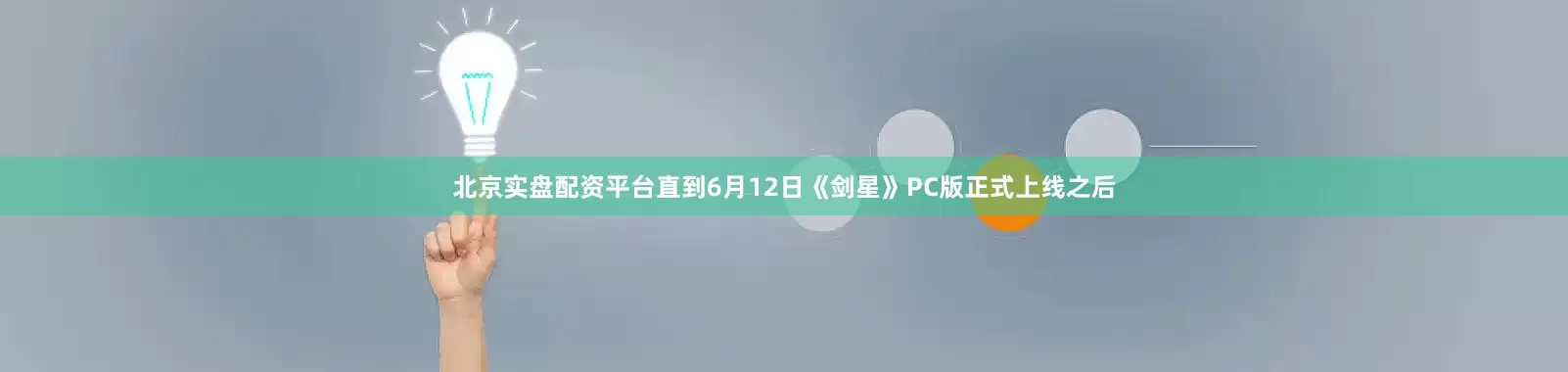老照片讲述:
一个女兵的西藏人生
上篇:
小序:欣闻电视连续剧《一路繁花》立项,我即刻转告伯母李国柱,还沉浸在老伴离去悲痛中的她,难得流露出微微的笑容,示意我抽出书橱里的《一个女兵的西藏人生》放在她的面前,双手轻轻抚摸着,听她曾给我讲述的进藏、在哪儿工作生活的往事,萦绕于我的脑际……

李国柱一生的履历中,最重要的也是最令人敬佩的是:她系首批进军西藏的女兵。她1949年参军,1950年军政大学毕业后从戎进藏,在那里工作了23年。她虽然出身贫寒,童年屡经战乱,由于从小读书,有学养的滋润,又个头高挑,仪表端庄大方,而雪域高原的风雨将她淬砺成了一朵英雄的。这里边即饱含着她矢志不渝的理想与责任,也不排除不久后她成为“首长夫人”的因素。



对于这段姻缘,有的人不太看好,觉得男方是军政要员,处事理智冷静坚毅,女方系涉世尚浅未曾淬火的学生,双方存在差异具有变数;再就是会不会成为首长身边的负担。李国柱听到后莞尔一笑,说:我是被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我如果爱你,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这一晃,他们不离不弃、相亲相依的走过了近七十个年头。回首这样两棵屹立在雪域高原上的大树:\"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 "(注)多象一幅笔力劲拔的油画,更象一首气韵恢宏的边塞诗。2008年,他们走进了“首届华夏盛世金婚大典”的殿堂,从国家部委领导同志手中接受了"百对金婚老人"的荣誉证书,这其中的人生百味恐怕常人难以体会,其含金量更是当下动辄分手的情男怨女们怎么也掂量不出来的。



人们常常以为“首长夫人”,总归茶来伸手饭来张口、衣食无忧、幸运而幸福的一类,而伯母工作在我国最原生态最艰苦的特殊地区,身处刚刚解放乱象丛生的特殊年代,肩负着解放和建设双重任务,特别是汉族官兵与藏族人民的沟通,藏族人民对汉族干部的认同接受,需要破冰,需要耐心,需要时日,更直接的是从自己和战友们的形象、言谈举止开始。她清楚这些,于是把自己的言行与所从事的事业,所扮演的角色紧密相连,事事带头,处处严格要求,总是以牺牲奉献为荣,以吃苦耐劳为乐。她一个如花似玉的年青姑娘,用自己生命的极限去挑战高原生存的极限。她同所有进藏的士兵一样,背着背包,徒步跋涉两三千公里到达西藏各国防要地,饱尝了高寒缺氧,忍饥受冻的滋味;她参加了昌都战役,负重急行军时,曾赤脚一天趟过13道冰河,断粮时曾啃过半生不熟的死牦牛肉;在修建康藏公路建设中,她和男同志一样,在海拔4800米路段,干着挖、挑、担、扛的重体力活。




刚解放的西藏形势严峻而复杂,统战工作、宣传引导基层群众和培训积极分子显得尤其重要。国柱伯母正好先后负责做社会和统战工作。她感觉到和藏族人民便于沟通的前提是熟悉藏语,于是,她下气力攻克藏语关,成为首批能说一口流利藏语的“通司切嘎”(半个翻译)。同时学会了骑马。 此后,她经常参加地委的工作组,下乡宣传中心工作,发放农贷、蹲点,并走家串户,诚恳耐心地做思想工作;1959年7月,为了为民主改革培养骨干力量,江孜地委创办政训班,培训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伯母一个人担任教员,培训了15期2000多人。其中许多学员后来成为各级各层的领导干部。再后来,为了稳定群众情绪、防止人员外流和发展当地生产,她带领工作组到地处边境的亚东县嘎林岗乡蹲点一年零两个月,繁重的工作艰苦的环境,使她患上了当地人常有的粗脖子病和肺结核,还有缺氧性的肝肿大九公分⋯⋯。一个女性,在那么艰险而复杂的边境地区,坚持工作那么长时间,在全西藏也是少有的。这一切一切正吻合了她作为树的形象与丈夫并肩站立的誓言,与常人想象的“首长夫人”的优裕相距甚远甚远。





为人妻任谁都得面对生儿育女。伯母于1953年和54年在海拔4010米的江孜分别生下了两个女儿,由于产前缺乏营养,孩子生下来脸瘦得不像样子,二女儿头骨上留下一条大大的缺缝,至今不能瘉合。两个孩子都在10个月大小的时候患上高原性心脏病,其中一个做了心脏大手术,取掉两根肋骨,不得不托人把孩子送往地处四川的西藏保育院。一岁两岁的孩子离开妈妈的怀抱,开始过半军事化的生活。有的孩子捡到带字的紙片,便反复地念叨:妈妈来信了,妈妈来信了!让女老师们听得忍不住掩面而泣。孩子们耳边听得多的是“叔叔”“阿姨”“老师”的称谓,对“爸爸”“妈妈”很生疏。孩子大一些,老师教他们给父母写信,孩子写来的几行字是妈妈眼中最宝贵的“圣经”,天天拿着看,无法控制地任由泪水打湿小小的信笺。伯母平静地叙说着这一切,不断地出现 “孩子没有享受到家庭的温暖”,“我们未尽到做父母的责任”一类的心灵呼喊,显而易见,她内心深处经受着多大的磨难,欠疚的感情潮水撞击着一个母亲最敏感的神经,难以排遣。
她第一次到四川学校看望孩子是在母女分别四年以后,孩子不认她,伤心地哭喊着:“你不是我妈妈”。经老师说服后认了,但仍然不会喊、不去喊“妈妈”,使本来就难受的妈妈更加难以承受。相见难,别亦难,大人尚且如此,何况和久别的孩子乍见骤分,难舍难离,想抱抱亲亲孩子,没想到孩子不解地问:“你为什么爱哭”? “我们就不爱哭!”一下子推开了妈妈……第二次再去看孩子是又隔了6年后的1962年。其间老师们议论:这学生的家长为什么这么久不来看孩子……这怎能说不是人间生离的一幕人伦惨剧。伯母奉献给她所钟情的那片土地的,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母亲的所有,她对于子女欠缺了最珍重最宝贵的东西——母爱,她用自己所承受的现实,诠释出了所有老西藏们“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沉重内涵。





与孩子由于久别而疏离的伤感还没有退去,肺结核和粗脖子病又一次来袭,只得住院治疗。就在这时,伯父从江孜专程赶到拉萨军区总医院来看望她。伯母看着一身军装的伯父觉得很反常:他那么忙怎么会专程过来呢,这是以前从没有的事。细谈后得知:伯父要参加对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上前线了,在整个西藏,就他是调回参战的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伯母一时楞住了,脑海里闪过的笫一个念头:打仗就会有牺牲,此去吉凶未卜!做为军人的妻子,只有服从和支持。于是她提出照张合影。其中的含义、份量是置身事外的人无法体味的。这张照片珍藏在她的影集中,更是珍藏在她的内心深处。此后的日子里总是提心吊胆,仅凭半月一张的《西藏日报》和广播关注着前方的战事。直到数月后伯父凯旋归来,并赴北京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她的心才总算放下。



“做女人难,做高原的母亲难,做参战军人的妻子更难”。伯母承受起了这些磨难,她把痛彻心腑的思子念夫之情,点点滴滴化作对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热爱和帮助,她在承受中脱颖,在转化中变得坚强高大。此后,她更加坚定地踏实地走进一座座百姓的宅院,握起一双双牛粪浸泡过的粗粝大手,用融进自己母爱与情爱的精神去慰藉去温暖藏族人民饱经沧桑的悲苦之心,交结了一批又一批上至高官、贵族与活佛、下至农奴与百姓的朋友。尽管她做的这一切,算不上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然而,她真诚的笑容,亲和的举止,春风化雨般地融入了那片佛山净水,长久地留驻在了藏族人民的心灵里……








伯母他们无怨无悔地奉献于那片雪域,那片雪域注定融入他们的生命里。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两位老人已赋闲,这并不能割舍他们与西藏的未了情缘,陆续回藏12次。















(未完待续)
注:引用诗句来自舒婷的《致橡树》
(作者注:本文插图均来自李国柱伯母及她的著作)
作者简介:
桑新华:1954年12月生,山东省肥城市人。中共党员,大学学士。2002年任泰安市教育局局长党委书记。期间兼任泰安高炮预备役政治部副主任。2015年退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第七届作家大会代表。

高开网配资-高开网配资官网-在线配资软件-在线股票配资官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